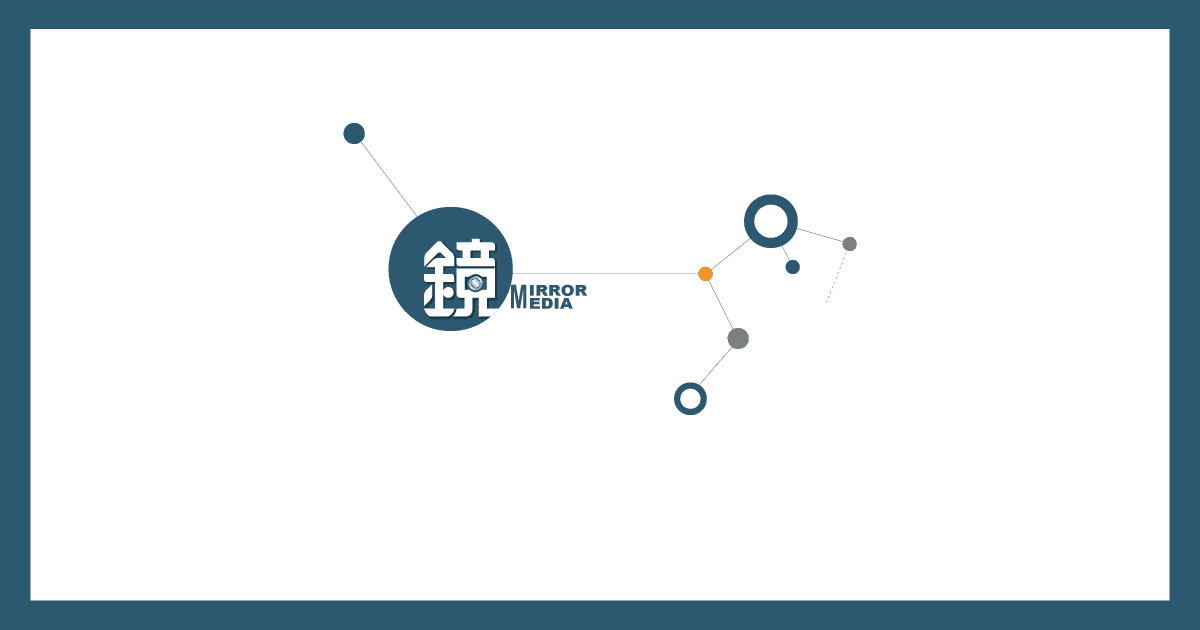雷光夏再說起一個關於創作的小故事,說完連自己都覺得有些荒謬而笑了起來。她老家是北投的日式老屋,作曲的房間有個天窗,她彈著歌,有小鳥飛來在天窗上走來走去,「我就想,這首歌是很好聽嗎?OK嗎?大概是好聽你才會過來吧。」她接著說,「那首歌,就是《第36個故事》的主題曲。後來它還得了金馬獎(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),好像真的小鳥是對的。」

「以前我家狗不能進屋子,但只要我開始寫曲,他們就會在前面踩腳墊那邊趴著,就會這樣聽這樣睡著。」其實一點都不荒謬,光想像就很有畫面,而如果能量是能被傳遞的,那麼眾生應該同樣都若有所感。
訪問雷光夏前,我尋求復古的形式,想找出某張實體專輯聽,卻怎麼找都找不到,我因而突然明白了時間原來可以是具象的。自問為什麼還是需要拿在手上聽的感覺呢?原來我們還是渴望一種有形,是時間的有形,是這張專輯出現在我們生命裡的時間,而且是深深連結記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