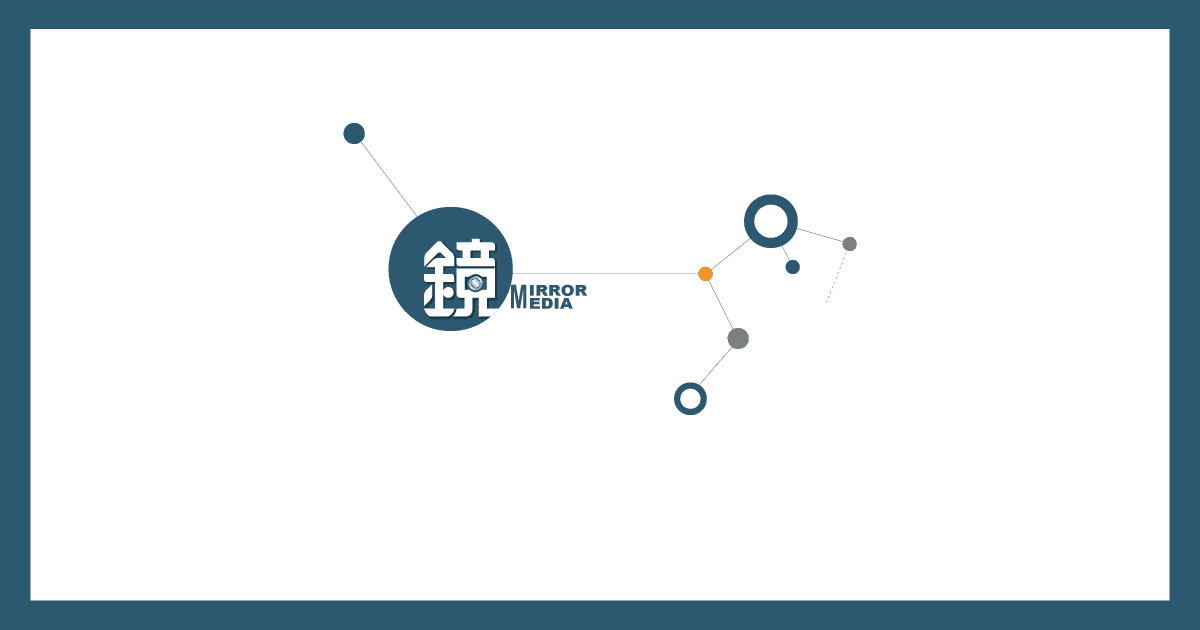拯救與謀殺,機會和命運,該如何計算得失?又能從那個角度展開思辯?喜歡哲學,又學了半輩子醫學的李明亮,關於死亡的選擇,或許能有新觀點?
事先讀過訪綱的他,好像也在等這一題,很理性地跟我說:「這個其實很簡單,看你要救一個還是救5個?」非常之「醫生」的回答,儘管他根本不是「那麼醫生」的一個人。
比方說,在可以保送台大醫科的時候,偏偏想念哲學,最後在父親的堅持下勉強「象徵性」地將哲學放在第二志願。我問他後悔嗎?他只說:「彼時陣憨啊。彼時陣我講我無想欲讀醫學系,阮爸爸足生氣。」也沒有掙扎,補充:「彼時陣哪會敢。阮那時陣爸爸會當打囡仔呢。」父親最後甚至以「念哲學的目容易自殺」告誡,李明哲只好妥協。

大學畢業,到美國進修後,就沒那麼聽話了。在美國待到8、9年時,父親在台南「林百貨的斜對面」幫他備好200坪左右的房子,待他回國開業。那應該是條一路坦途的路,但李明亮不走,回答父親:「我不會回去,即使回去我也不會開業。」聽起來很叛逆,但其實就是在美國找到了了自己的志向:遺傳醫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