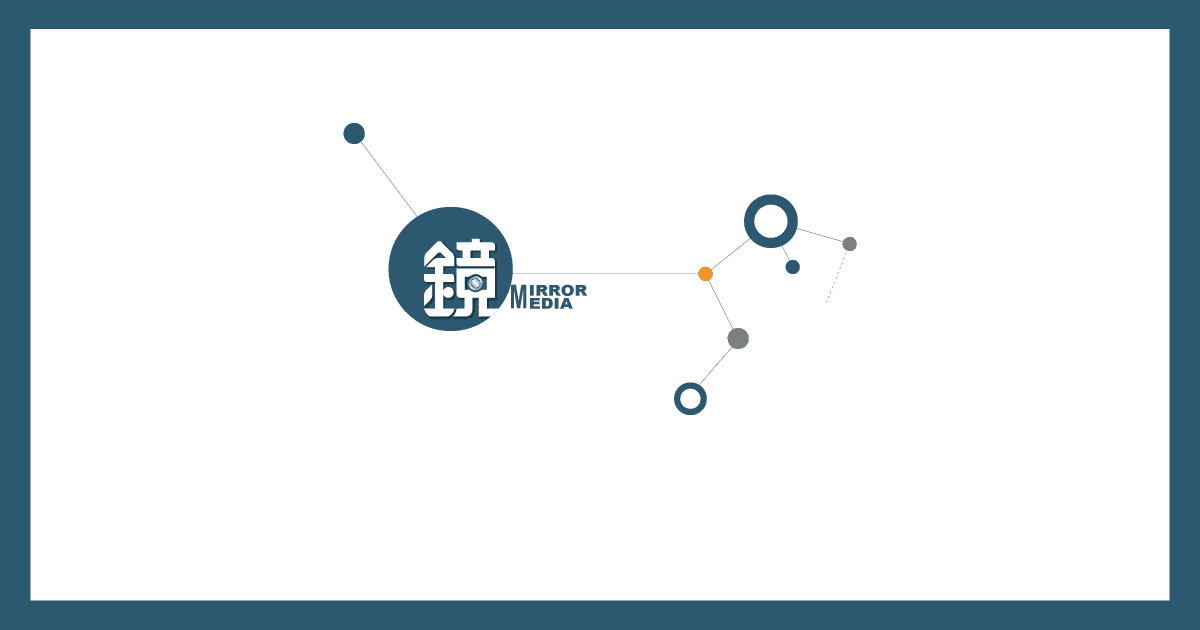為何當初同婚專法是這樣立的?時間回到2018年公投,反同方大勝的社會氛圍讓立法者感受到政治壓力。民進黨前立委、尤美女律師回憶2019年立法時:「當時反同方堅持大法官只解釋婚姻,沒解釋子女,不能超出大法官解釋,認為收養小孩有損兒少利益。協商時,我們說很多同志已經有孩子了,總不能不處理吧?折衝到最後,只能處理現有的繼親收養親生子女(意即接續收養對方經人工生殖、或與前妻前夫之親生子女)。」
反同方認為,同志家庭長大的孩子可能面臨自卑感、學業不佳、性別認同混亂,受到性騷擾、犯罪、家暴的比例比一般異性戀傳統家庭更高。愛護家庭大聯盟秘書長張守一說:「國外有很多這樣的研究,台灣走在其他同婚合法國家後面,應該要借鑒。」

無黨籍立委林昶佐(時為時代力量立委)2019年曾與同運團體合作提出草案版本,其中一條開放同性配偶共同收養,但他坦言,遊說過程發現連要保住「婚姻」二字都很困難,有些立委礙於公投結果而不敢支持,守住婚姻二字已是底線。包括共同收養、跨國伴侶、人工生殖成為難以觸及的深水區,最終只能支持行政院提出的草案版本,再改任何一個字都有可能無法通過。針對無血緣收養,林昶佐說:「收養應回歸專業評估,同性配偶若是適合的收養人,立法者不應因同性配偶身分限制。如今公投已經過了二年,可以回頭重新檢討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