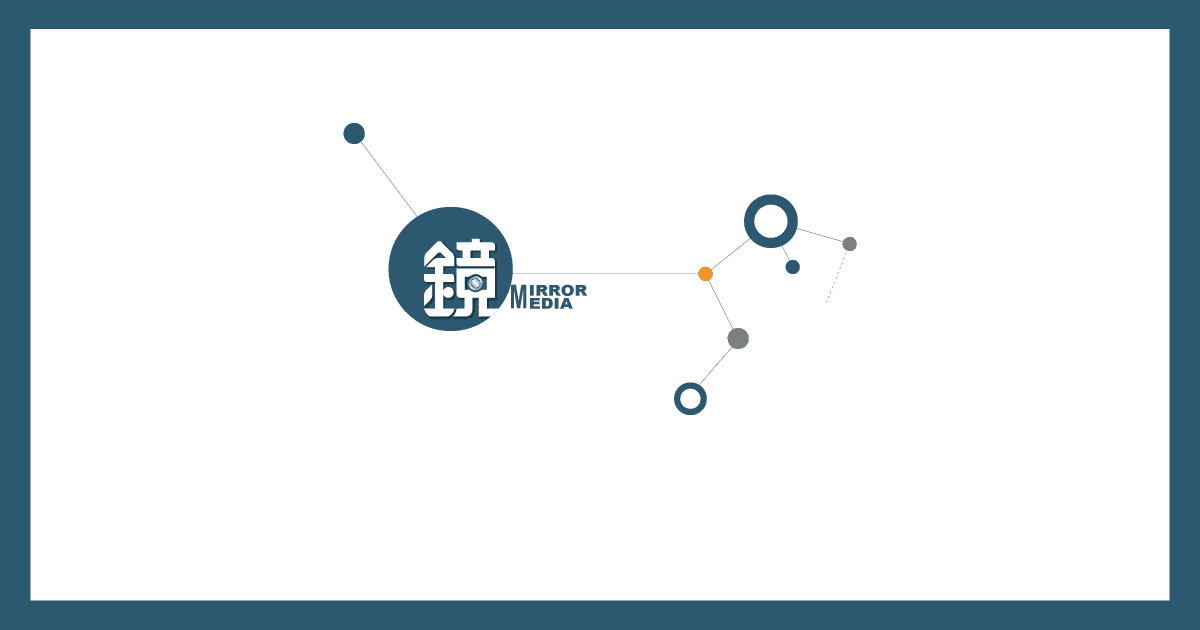她臉上掛著淺笑,語氣暗下來:「那陣子,我有時會忽然很有信心,有時又忽然很絕望,絕望不是心虛,自己當然知道自己沒有做的事,可是那股絕望是有一種不相信人家會聽得懂而且還相信你,明明你要講的是真的,所以開始對世界產生不信任,可是沒辦法,還是得一天一天克服。」打官司如芒刺在背,隱隱的不是痛,是想起來就搔癢。
日復一日被壓力占據,食無滋味,從55公斤瀕臨跌破四字頭,她驚覺這世界並不如想像中簡單。為了不崩潰,她逼自己寫專欄、出席講座、修行密宗,「可是心底一直有個懸而未決的事情,笑也沒辦法盡情笑,我覺得語言無味,跟人的互動也很無趣。」相較於過往意氣風發,此刻真是跌落谷底,到底了,反而會看見許多不曾在意的陰暗面。
「當年看完檢調訊問我同事們的口供,我心想,他們是不是真的很討厭我?在陳述中我就像是跋扈的女人,非常惹人厭,我有一種『我真是這樣嗎?』的感覺。我是不是在別人眼中好像各種條件不錯就覺得自己很驕傲?有段時間我不斷自我否定,厭惡身上『北一女、台大、留學回國的菁英分子』習性,像是忽然打開了天線,啊,妳可能自以為很善良,可是別人都討厭妳喔,那妳在不在乎?」